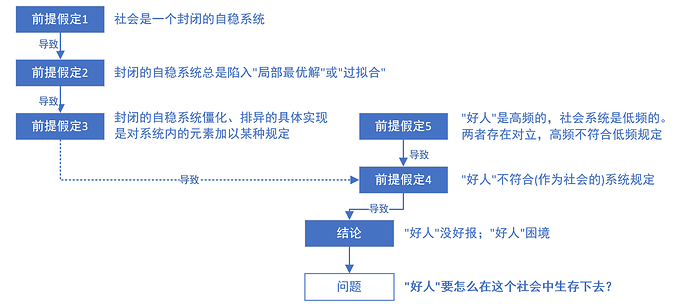这一点我能以我自己的生活经验观察举一个例子。现在另起一贴来举例。
1.背景概述
大概在去年的这个时候,我在长沙的某个餐馆里当服务员。
有一个同事,就比较符合贴主对"好人"特征的描述。他很负责,有原则,并且本来不善社交的他,在极力地假装自己善于社交。对每一个人友善,对待顾客也会非常贴心、服务周到。
并且他还有着一颗理想本心——虽然是在当服务员,但是还是有着"达则兼济天下"的救世济民之心。想要改变整个制度。他其实是个本科生,想考公入仕,“至少在自己能力范围内,去庇护一方人民”。来当服务员只是权宜之计,应付一下当前的生活。
我们的那个餐馆,是一个连锁店。庙小妖风大,通过压力下属来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转。高层管理PUA各个店长,各个店长又在PUA自己的店员。每天都向员工兜售焦虑来让员工"奋斗"。再加上我们的那个店长,又是一个比较喜欢耍心计的人,整个店的氛围更是乌烟瘴气。他很看不惯这一点,性情刚烈,会直接怼店长。
但是我要说的故事不是关于店里的"权谋斗争"的故事,而是从一件小事开始说起。
2.命运预兆
有一天晚上,一伙客人来店里喝酒,很嗨。结完账后还在酒桌上面红耳赤侃侃而谈。那天是他负责收银,但是顾客却少给了几块钱。
他发现了这个情况,但是却不敢声张,因为那几个客人看起来都比较"社会",再加上已经喝上头了,他害怕会因为几块钱的事情引起纷争。
这个时候,有另外一个服务员在旁边多少有些幸灾乐祸的"指指点点",用那种"巧妙的话术"去贬抑他的人格,明里暗里嘲讽他做事不力(没错,当时那个店的氛围真的很不好,就这点事都还值得说道一番。当然,这可能是店长的"权谋"让服务员们不太团结分而治之的结果)。
他不敢去找客人补钱,(在加上某人的引导)于是安慰自己:这都是自己办事不利,自己应该承担这个后果。于是拿出手机来准备自己把客人的钱给付了。
我按住了他,说这并不是他的责任,而是客户自己没有把钱付完,可以去找客人要。
但是碍于客人"黑恶势力"的感觉,他坚持认为这是自己没有看清楚的结果,然后开始论证自己补钱是多么合理。自己应该要如何负责。
我说:吃饭付钱,天经地义。你不要把责任总是往自己身上揽(我在之前就发现他有这个习惯)。负责不是这么负的,你要明确自己和他人的责任,不是你该付的钱,你坚决不要付。不要做滥好人。你这次付了,下次还是会有同样的事情找上你的。因为你这样处理事务,就会让生活的各种情况骑在你头上。
那时他表现得很不理解,当时我们之间甚至有些对立。因为我的态度非常坚决。他觉得我根本就没必要这么"上纲上线",“就是几块钱的事情而已”。
最终,我见局面有些僵持,就自己拿着收据走到那一桌客人面前,跟他们说还有钱没付,请去收银台把钱结了。他们也并没有不怎么讲道理,而是确认账目之后把钱结清了。
但是没有想到,我说的那句话,最终可能"一语成谶"。
3.命运重演
最终我们都离开了那个餐馆。在长沙继续呆了一段时间后,他回他的老家。
旅行在火车上,我的同事当时水杯里盛满了开水,想要让它冷下来,于是开着盖子放在了火车的桌子上,由于火车毫无预警的急刹车(这种情况相当少见,但是却被我的那个同事遇到了),水杯倾倒,洒出来的水烫到了坐在对面的另一个顾客。
对面表现得很痛苦,乘务员也过来查看情况。我的同事不知所措。接着他应该是提前下站(到受伤乘客的目的地),去处理事后问题。
对方可能是一个务工返乡的农民家庭,应该是两口子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家,烫伤的应该是其中的女方。但是却狮子大开口,张口就要五六千的赔偿费。这我本就不富裕的同事当然承担不起。于是报警,让公安、铁路系统、对方和我同事几方一起处理这个问题。
铁路系统主张"这不关他们的事情",是我同事的个人责任。
对方不管怎么样,要赔偿,要治疗。
公安系统则是想着快点把这个事情解决,见铁路系统在踢皮球,也顺着他们的话对我同事施压。
我同事则感觉到很迷茫、很无助。
在火车站纠结了好久。最终我同事的恻隐之心犯了。他看到对方衣着巴巴,感觉对方打工也生活不易。而且不管如何,至少应该先去带他们医院看看。于是责任的扯皮被搁置。但是这一去,就去出问题了。
首先对方莫名其妙地指定要求去一家医院(应该是当地最好地医院),治疗要是最好的,药也是用最好的,反正两天下来不知道怎么情况,一下就花了两千多。我同事当时看到账单感觉天都塌了(毕竟身上当时也不会剩下多少钱)。
而且一离开火车站,铁路系统和公安系统就再也不管了。我同事找上他们,他们也是继续踢皮球。
最终在那个地方左右折腾了应该有一个星期,我同事感觉实在不能纠结下去了。于是就直接走了。对方似乎还扬言要继续报警,但是我同事决定就直接离开,最终警察也没有找上门来。
4.事后总结
最终我是在我同事和我打电话的事后知道这件事的,他说我在餐馆里说的那句话,他当时还不理解。结果它真的发生了。我们在电话中进行了事后总结。
我的同事在电话里回顾,其实当时就不应该离开火车站,要把责任理清楚再说。
这件事我同事是否有责任?或许可以说有,但是很小,至少不是主要责任,因为谁也不会预料到火车会突然刹车。这更多的只能是铁道系统自己的问题。但是铁道部门也不愿意担责,将之转嫁给普通人头上。
为什么最终却是我同事一个人在负责?因为在这里的每一方都在欺凌弱小,都在把枪口指着那个"好人"。但是"好人"在这里,其实仍然有选择的余地——他可以不选择做一个"好人"。
因为能够在那里扯上半天皮,就一定意味着这并不是被规定死了的东西,而是有洽谈的余地的。但是我同事却最终选择把责任全部揽下,只是因为"觉得对方可怜"。结果他发现,“真正可怜的是自己”。
一来是在那个时候他的确感到很恐慌、很迷茫,所以处于一种被动的情绪中。但是这个被动情绪是自己感觉"犯了错事"的潜意识认知结果,恐惧感充满了他,于是变得非常迷茫。事实上,没有错误。只是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情,仅此而已。
二来是未平衡的对苦难之同情心,导致没有理清责任就离开谈判场所。结果最终责任还是没有理清,自己背负了全部的苦果。这里一方面是太急于结束当前"负罪感"的状况(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不平衡的情况);另一方面则是需要看见:对方并不比他更可怜,其实谁也不欠谁,大家都是苦命人。
就这样,"好人"没有好报,显化为一种很黯淡、很不可抵抗的局面。但是往往自我对自身的知晓就会在其中发生,并且越能够接纳自我的完整性。这类事情对好人的伤害,其实就会越小。而这只能显化于实践的细节,而非理论中。